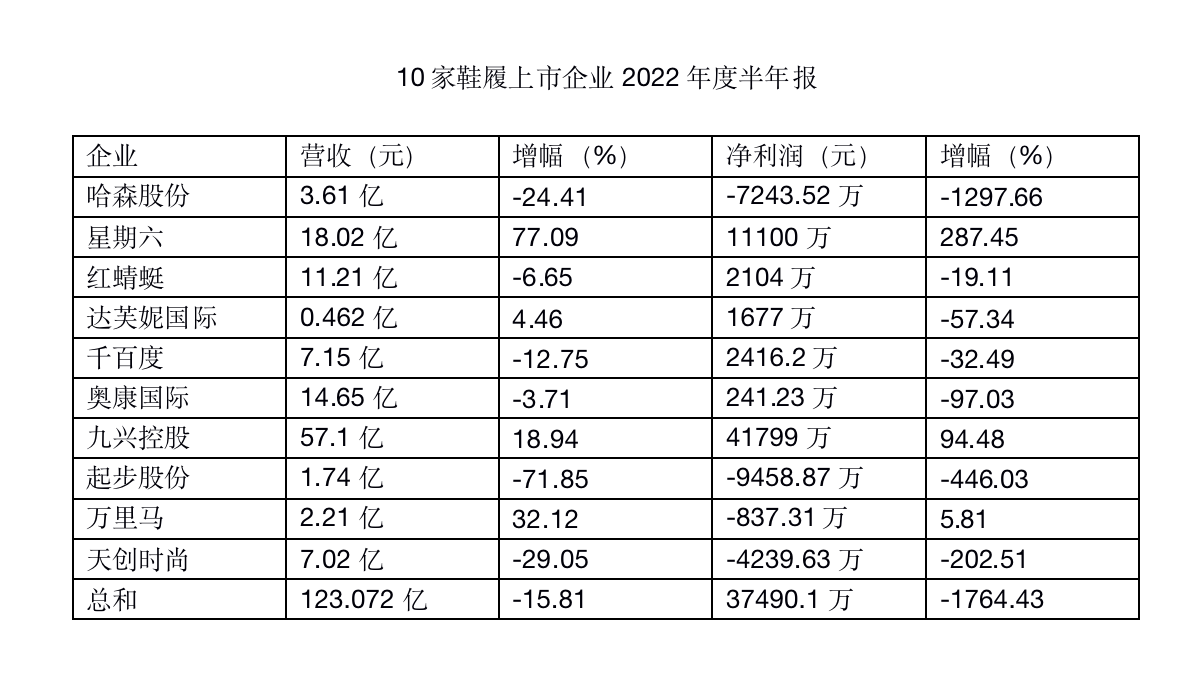长髯人进门后,将砍柴板斧放于门后,掸了掸身上的尘土,问学童说:“那位来客就是我的老师冯公吗?”学童们齐声回答:“是的。”长髯人就走上前来跪下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说:“山野村夫,凡夫俗子,苦无名师指点,真是以管窥豹,坐井观天,闭塞卑陋至极。蒙先生锤炼,不吝啬畅教,得以重建天日,心境豁然开朗,就像盲人复明,如大梦初醒,真是说不尽的感激与惭愧。”冯生急忙答拜,并且扶起他来,说:“先生真是天下奇才,能在此荒郊僻野认识你这位朋友,我还怕是高攀了,要是妄自称大,以先生自居,岂不是太罪过了吗?
两人就此相互告坐,彼此自我介绍了乡村籍贯,接着议论历史成败。谈说经学、史学、理学,髯樵都能对答如流,说中要害,真可以说是心如细发,见解精辟。不知不觉间已是日落西山,冯生还是恋恋不舍的不肯离去。髯樵说:“贵客光临,蓬门何幸,可惜这破庙荒凉不堪,无法让你安顿,怎么办?怎么办?”冯生笑笑说:“与你相交,实在是我一生中的乐事,我想上你家去,拜见令堂大人。”髯樵知道无法推阻,就放了学,让学童们回家,将门锁上,请冯生骑马而行,自己在前面领路,慢慢的在田野小路里走着。
他们来到颜家坳时,已是夕阳垂地的时分了,看见有三间茅屋,简陋得仅能遮挡风雨,但门户庭院十分整洁,几案床榻安置得十分得当,一位白髯老婆婆倚靠门边正抬头眺望,那就是髯樵的母亲。冯生胯下马来,对颜母下拜行礼。颜母说:“何方贵客,光临寒舍,如此谦恭有礼,使我心中不安。”髯樵跪下禀告了冯生的来历,颜母又是高兴又是敬重。髯樵则点起灯笼出门卖酒,嘱咐妻子煮了一尾鲤鱼,做起饭来。冯生吃得酒醉饭饱,晚上就睡在他家草席上。髯樵进内房看见母亲是否睡稳之后,着才出来料理马匹备好食料。似乎一刻也没有空闲过。第二天早晨冯生起床,髯樵已拿来毛巾脸盆请他洗浴,又端进热气腾腾的煨芋头,当做早餐。餐后冯生向颜母拜别,恳切地劝髯樵去考秀才,说:“以你这样的人才,难道还够不上和那一班碌碌之辈共享荣华富贵吗?倘若你要自命清高,难道就不怕被为老母着想屈尊做官的毛义嗤笑吗?”髯樵诺诺而应。
冯生回到官衙后,在知府跟前竭力吹嘘推荐,说:“谁说荒郊野外隐居生活的寒士中没有杰出的人才呢?”边说边朗诵髯樵的文章,书声朗朗。知府笑笑说:“他已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胸怀,由你替他宣扬,你们倾心相交,的的确确难能可贵,你也可以说是爱才若渴了。话虽如此说,但是提拔英才,确是我这知府的职责所在,向高人劝架,要他出山应试,那只有由你去任劳了。”不久府中将要开考,冯生急忙来到山中,从自己薪俸中取出俸银20两送给髯樵,使他无后顾之忧。髯樵不肯接受这笔钱,冯生硬要他接受,劝说得几乎要哭出来了,髯樵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,这才收下银子,怅惘地随冯生来到府城。
考试结束后发榜,髯樵竟高中第一名。学台大人莅临岳阳州府,读了髯樵的文章,大为惊叹,说:”该生文章融汇经学,出入风雅,不是潜心钻研古代时文大家十多年的人是达不到这样的妙境的。”就推荐他进了县学。
这年秋天,朝廷举行大比。冯生去问髯樵:“你屈居在贫困境地已经多年,现在到了一展宏图的时候了。举子三年期待奋发,就在此片刻之间,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进省赶考?”髯樵愣愣的,不能回答。冯生知道他经济困难,就替他向知府告禀,知府也是惜才之人,当即很慷慨地拿出五十两银子送给髯樵,请冯生捎去。髯樵死也不肯接受这笔馈赠。冯生发怒说:“这不是偷盗,贪污所得的钱,这是知府大人多年的积存,你今天受到知府大人的知遇之恩,将来一旦高中,就去报答他就是了,有什么可耻的?”曾继祖